中国改革的终结与重启–关于改革路径之争的思考
荣剑博士

冷战以来形成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现代化的路径之争。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不仅使苏联、东欧以及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深信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之路,而且也对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后殖民时代告别西方统治的主要制度选择。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世界性潮流,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被共产党人宣布为是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制度,这个对人类理想社会的庄严承诺鼓舞了众多国家的领导人加入到社会主义行列中。但是,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起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生了矛盾,所有标榜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未像他们的领导人所承诺的那样,在生产力上超越了西方国家并给予人民公平和公正的生活。相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权力腐败、社会不公和官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国有经济长期处在效率低下状态,国家治理体系遭遇了沉重的危机。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过总结:
“命运是这么安排的,我成为国家首脑时就已经明白,国家有问题。资源很丰富:土地、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还有智慧和人才。上帝没有亏待我们,而我们的生活比发达国家差得多,越来越落后于它们。
原因已经是显而易见的——在官僚指挥体制的束缚中,社会窒息了。国家注定要操纵意识形态和承受军备竞赛的可怕负担,已经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1]
正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竞争中,以及在竞争中日益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成果和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迫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走上改革之路。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11日任苏共总书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的核心要求是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个目标,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于1985年12月上书戈尔巴乔夫,论证了把苏共分成两个党的必要性,认为“两个党就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社会也就能从中获得强大的活力。”[2]从这个主张出发,雅科夫列夫设计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强调了改革的首要原则是民主,民主的突破口就是选举,要求总统通过全民直接投票,“从加入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各党提出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任期十年”。[3]但是,戈尔巴乔夫对这个改革主张“虽感兴趣但不热烈”,他认为这些想法为时过早了些。此时,戈尔巴乔夫刚刚获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既不愿意制造一个政治对手来分享他的权力,也不愿意相信苏共的政治危机可以通过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他深信苏共可以通过自我改革——不从根本上动摇党的统治地位——承担起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
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时间仅仅持续了六年便终结了。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同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由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在苏联总统岗位上的活动。”[4]第二天,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向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移交了国家最高权力,苏联终结了,改革也彻底终结了。雅科夫列夫后来认为,改革看起来是结束于1991年“八一九事件”,[5]其实早在1987-1988年期间已经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改革”。“社会中的对抗情绪迅速增长,衰颓不堪、已无形磨损但仍进行统治的机构已经看到将丢掉政权的威胁。”[6]后来的政治危机则进一步加速了改革的解构进程。戈尔巴乔夫在辞去总统之后也认识到了:“改革半途而废,甚至不如说在一开始就中断了,这是令人痛苦的。”[7]他认为改革进程是“被那些不赞同改革和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打断的”,改革的反对派既有党内的“保守主义者”,也有党外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叶利钦成了极端反对派的政治领袖。“就这样,改革在保守派和极端民主派势力的打击下中断”。[8]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认为,改革年代完成的事情在继续产生影响,回到过去变得不可能,改革的主要成就是俄罗斯公民获得了自由,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共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无疑是20世纪的历史性巨变,被霍布斯鲍姆视为是20世纪的提前终结,也被弗朗西斯·福山视为是历史的终结。尽管这些关于“世纪”和“历史”终结的预言未必契合后来的国际秩序重构,但苏联解体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全面崩溃,对世界形势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更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至少让邓小平重新意识到了,重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只能走进死胡同,必须继续进行改革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用傅高义的话来说,邓“在1992年取得了戏剧性突破”,他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反复阐述改革的重要性,并且提到:“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9]正是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共在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使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南巡讲话”到中共“十四大”,中共迅速从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了出来。在傅高义看来,邓的南方之行并没有使谨慎的计划派和正统的意识形态宣传家闭口不言,但“改革开放成了不可逆转的政策,重新关上1978年后打开的大门已经不可能。”[10]
在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彻底终结之后,中共自1992年重新启动的改革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改革还是“原来意义上的改革”吗?
朱学勤在2018年的一次内部学术讲座中,以“四十年和二手时间”为题,提供了关于时间政治学的一个独特分析框架,他借助于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创造的“二手时间”这个概念,将二手时间定位于新的统治者只能在前任统治者的时间里运行,不敢或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手时间。按此概念判断,邓的改革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手时间,但改革在1989年便已终止,以后在改革名义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不能称之为改革。朱学勤还认为,从世界改革史来看,各国改革的平均时间是7-8年,如果不能在10年内解决问题,改革就是失败了。[11]
中国改革是否终结于1989年,关键是看改革如何定义。1980年代存在着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边缘力量自发推动的改革,由此构成了改革的二元结构。政府主导的改革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农村领域承诺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增加粮食进口,提高农民粮食消费的数量,鼓励副业发展,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在工业领域要求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速对轻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产领域的政府开支,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面,推出“放权让利”政策,赋予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提高它们的积极性。所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有一定的效果,却没有将国有企业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更不用说对经济体制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由此可见,政府主导的改革从一开始起就不是彻底的,我谓之“没有思想的改革”,即改革没有理论,改革的实际情况是理论落后于实践,不是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实践如何突破理论,突破理论所设置的限制。[12]与政府主导的改革相比,科斯概括的由四种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真正构成了对旧体制的革命性突破,对中国市场化转型具有根本性影响,带来的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和倡导“公开性”,在1980年代中期曾经成为中国党内外“改革派”力图借鉴的模式,即改革首先是要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这和邓小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苏共的改革似乎比中共的改革更为激进。戈尔巴乔夫后来在解释别人经常问他的“为什么我们没有与政治改革一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了苏联保守势力太强大太顽固,以致苏共中央委员会在1987年4月通过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初决定无法执行。[13]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中苏的不同改革路径,源于不同的国度、文化和初始条件,苏联不首先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根本无法启动,苏联走不了“邓小平的改革之路”。他认为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能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保证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他在承认苏联改革失败的同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对于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14]
戈尔巴乔夫对中国改革的评价反映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中国问题研究者的看法,中国改革并未止步于苏联的解体,相反,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起,中国开启了远比1980年代规模更为宏大的改革进程。由此带给人们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急剧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长期受制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的中共领导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向市场经济观念的转变?
张五常为回答这个问题下足了功夫。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于1982年去香港担任教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让他占据了“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这个决定也是在他的老师科斯教授的鼓励下作出的。张五常在1982年发表了石破天惊的文章——《中国是否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15]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他的肯定性“推断”表示怀疑,张五常也对自己的结论表现出审慎的态度,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大致需要五十年时间。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之快,远远超乎经济学家的想象,以致张五常在1986年就不得不对他的观点作出调整,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至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张五常心目中,中国改革已经成功,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被其视为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既精彩又重要”。[16]他为此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就是试图从经济学理论上阐释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
张五常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1980年,但“中国经济的奇迹发展不是八十年代,而是九十年代”,[17]原因在于,中国改革从九十年代之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区竞争”模式。他解释说是在1994年开始领略到中国经济制度的“超凡之处”,在1997年认识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在2004年底解通了这个制度运作的“密码”:“中国的地区竞争自成一家,天下独有”。[18]
张五常把中国的“地区竞争”概述为“县际竞争”模式,为此提出了“承包合约扩张”的概念来解释“县际竞争”,认为各自负有承包责任的地区成为互相竞争的主体,首当其冲者当为县级政权。中国最大的经济权力不在省市和村镇,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里,因为县有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户与户之间的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竞争,均赶不上以县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决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
张五常在前后间隔差不多近30年时间里,分别用市场经济和“县际竞争”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来认识它们各自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确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是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科斯在2008年完全赞同张五常用“县际竞争”说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分析,但他在2012年部分改变了这个看法,认为张五常分析框架的弱点在于:
“它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19]
科斯对张五常迟来的批评,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制度的进一步认识。一方面,他认为制度的变迁是历史性的,八十年代的“边缘革命”为九十年代的改革创造了前提性条件,政府及其国有经济体系在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积极作用,它们能否在九十年代革故鼎新并成为推动市场经济的正面力量,是需要质疑的。另一方面,科斯认识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20]
科斯认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取得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开放社会与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道德与知识基石。”[21]
科斯在2012年对“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的思考,具有先知性的意义。虽然他强调的“边缘革命”对于中国市场转型的巨大推动作用在1990年代的改革进程中处在不断衰竭状态,但沿着他的思路前进是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并非如张五常所阐述的那样,因为同时具备了市场和政府的两个巨轮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只是看到了各级政府在“地区竞争”中所焕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家(政府)主导的市场发展模式最终会演变成一个国家主义的控制模式,一个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的国家“利维坦”,最终将会吞噬社会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开拓出来的生存空间。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曾经认为,中国1990年代的改革造成了一个“大社会”和“大政府”共处的局面,一种平衡的状况。这个判断大致符合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20年里(1992-2012)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但黎安友对2012年之后的中国发展状况存有极大的疑问:
“社会多元和威权怎么能够共存”?“中产阶级和政府合作就是一个多元社会和威权制度共存的一个条件,合作就是社会和国家的合作。现在合作是不是慢慢减少了,为什么减少?为什么中产阶级现在对政权的态度发生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不是经济因素,因为经济还在发展。”[22]
黎安友的思考显然涉及到了中国市场转型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变。如果说张五常在2008年之前有理由认为“单靠市场的自由选择是不可以达到中国制度的合约组织的”,必须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以及“县际竞争”来达成中国特有的市场模式;那么,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以及中共政权和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平衡,究竟能够维持多久?事实上,从2012年起,这样的平衡已经被逐步打破了,直至今天,市场组织在国家机器的不断碾压之下,正在大幅变形,地方政府的“县际竞争”模式并没有培养起独立健全的市场主体,反而是形成了庞大的地方债务,民营企业沦为政府的附庸。“大政府”和“大社会”的共处模式或将重新演变为一个全能政府控制所有社会领域的国家主义模式。
综上所述,可以对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加以“政治时间学”的分类,亦是对中国改革在不同时期的性质加以分类化界定。1980年代由民间边缘力量所推动的“边缘革命”,奠定了改革的基础,开拓了改革的基本局面。但进入1990年代之后,民间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模式便被国家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模式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朱学勤所说的“改革终结”的结论是成立的。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至2012年,中国改革似乎进入了一个“黄金二十年”,这是“大政府”和“大社会”的共处时期,政府和市场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双重动力。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诸如张五常的“县际竞争”说和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甚至“中国即将统治世界”的各种说法,充分反映出中国进入了一个“自信的时代”——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23]自信意味着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不需要再改革了,改革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合法性话语。
中国的改革,不管是终结于1989年,还是重启于1992年,抑或再次终结于2012年,在改革名义下所发生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各种矛盾的剧烈动荡和思想领域的深刻分化及其冲突,均标志着中国的确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潮时刻。改革的肇启与终结是中国第三次社会大转型的一个历史阶段,[24]是从“革命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一次转型实验,实验是否成功或失败尽管还有待于历史的进一步界定,但改革制造了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时代前提和制度前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古今之争、东西之争、左右之争和文野(文明与野蛮)之争,都是在这个时代前提和制度前提下展开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左翼问题当然也必须置于在时代和制度的维度中加以认识和评价。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说过:“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他引用了一个阿拉伯谚语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25]
[1]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石国雄、杨正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6页。
[2] [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05页。
[3] 同上书,第211页。
[4]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5-6页。
[5] 苏联“八一九事件”: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党内保守派,联合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等党内权势人物,发动政变,宣布全国紧急状态,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总统。叶利钦拒不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发动人民反击。8月20日,莫斯科实行宵禁。8月21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政变失败。“八一九”事件加速了苏共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
[6] [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202页。
[7]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5页。
[8] 同上书,第392页。
[9] 转引自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620页。
[10] 同上书,第636页。
[11] 2018年6月29日,朱学勤在北京天则研究所做了题为《四十年与二手时间》的学术讲座,我被邀请担任该讲座的学术评议之一,讲座内容和评议意见尚未公开发表。我在自媒体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我们还将在“二手时间”里生活多久?》。
[12] 2013年年初,我在北京天则研究所第469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题为“没有思想的中国”的演讲,其中谈到了“没有思想的改革”,认为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是中共关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是中共近三十多年来在即有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讲得最彻底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讲过比这更重的话了。但这篇文章发表后就被束之高阁,连邓自己都不想实行,他实际上也意识到这篇文章提出的改革设想——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党内已经很难执行了,阻力太大,执行起来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我的这篇演讲稿收录于《山重水复的中国:荣剑演讲及对话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5页。
[13] 参阅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90页。
[14] 同上书,第369页。
[15] 在张五常的汉译著述中,“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同义语,这种去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在1980年代的中国,具有极大的思想冲击力,但张五常后来显然有意忽视了中共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定义,即用“社会主义”来定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置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不仅仅是一种宣传策略,而是体现了中共的市场经济的实质——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
[16]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第21页。
[17] 同上书,第26页。
[18] 同上书,第143页。
[19] [美]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第218页。
[20] 同上书,第253页。
[21] 同上书,第265页。
[22] 2012年7月,我和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Nathan)教授进行了一次长篇对话:中国制度的转型与韧性,上述观点引自对话,文本参阅荣剑:《山重水复的中国:荣剑演讲及对话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20页。
[23] 2012年11月,中共召开“十八大”,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本次大会产生了中共新的领导集团。参阅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主编:《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水史1921-2017》,第386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四个自信”,增加了“文化自信”,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24] 中国历史上已有两次社会巨变。第一次是殷周之变,周革殷命,封邦建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转型,其实质是夏商二代的部族联盟向西周的封建诸侯联邦转型,是氏族的国家形态向封建的国家形态的过渡和演进。第二次是周秦之变,秦统一六国,建立帝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其实质是封建的国家形态向帝国(帝制)的国家形态转型。第三次社会转型肇始于辛亥革命,革命终结了帝制,这是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亦是革命国家向现代国家、专制国家向宪政国家的转型。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还在持续中。关于中国历史上两次社会转型的论述,参阅荣剑:《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文史哲》,2008年第四期。
[25]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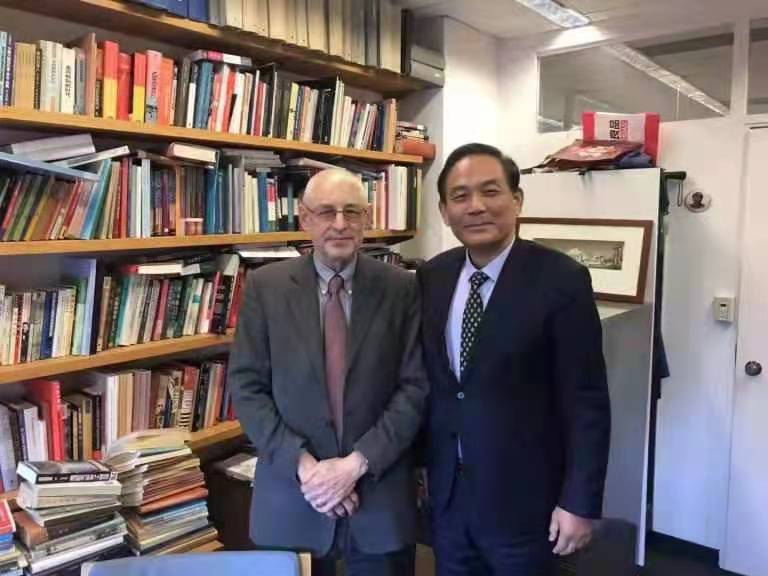
2012年,荣剑博士在美国访问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黎安友教授。




